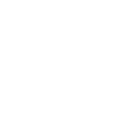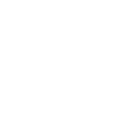乐鱼体育,LEYU乐鱼体育官方网站,乐鱼体育靠谱吗,乐鱼体育app,乐鱼体育官网

单以逻辑而论,当惠施对庄周所说“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提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质疑时,质疑者就已经处在自相矛盾中了。惠施问难的一个前提性预设是:唯有鱼才知道“鱼之乐”;由这个前提,他有了他的似乎理所必致的推断:庄周“非鱼”,所以庄周无从知道“鱼之乐”。然而,他忽略了这样一点,即他的前提性预设既是对庄周能否知“鱼之乐”的限定,却也是对他是否有权就“鱼之乐”向庄周问难的限定。因为所谓唯有鱼才知道“鱼之乐”的预设,必当引出唯有庄周才知道庄周之感受的推论,而依这样一个推论,惠施既然不是庄周本人,他便无从了解庄周的所思所感,因而未可对庄周之所言说三道四。正是看准了个中的破绽,庄周反诘惠施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诚然,即使在这时,惠施仍可以从自相牴牾的困境中为自己多少争回一点主动的:他完全可以申明他只是在类属(人类与鱼类)之间划了一道相互不可晓知的界限,并未把这界限延伸到同类中的个体(如人这个类中的庄周和惠施)之间。但他没有这样做,反倒是把很成问题的逻辑推演到了极端:“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于是,在这逻辑的彻底处,庄周开始“循其本”而折辩。倘作一种寻源竟委的检讨,可以说,惠施由所谓“非鱼”而“不知鱼”招致的“非子”而“不知子”的断语,即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既然自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那便不应当对自己所“不知”的对象妄加责问,责问自己所不当责问者,乃是责问者的逻辑的失误。换一种说法,“非鱼”而“不知鱼”、“非子”而“不知子”这一逻辑预设,是为惠施认可而不为庄周认可的;不为庄周认可的前提在逻辑上不构成对庄周的限制,为惠施认可的前提则构成对惠施的制约 —— 它要求“非子”而“不知子”者对其所称之“子”终止判断。因此,以“子之不知鱼之乐”在自己所当终止判断的地方下判断,使如此作判断者陷于自相扞格的境地。
但问题并不只在于逻辑的乖失,重要的还在于作为逻辑推理的前提的悬设。从“子非鱼”而“不知鱼之乐”到“我非子,固不知子”,“知”被作这样的限定无异于昭布万物和他人的不可知,而这不仅有违于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庄子·齐物论》,下引该书只注篇名)之旨,也有违于惠施由“合同异”而提出的“天地一体”(《天下》)的拟论。在庄子看来,万物都有着同一种源(“万物皆种也”),它们以不同形体相嬗替(“以不同形相禅”)。由同一种源来,又回到同一种源去,如同环那样首尾相衔(“始卒若环”),无从理清它的伦次(“莫得其伦”),其所遵从的是被称为“天均”(《寓言》)的自然均平之理。他由“相禅”淡化以至消解了“不同形”的物与物之间的界限和对立,并由这物与物之间的界限和对立的淡化启示人们泯除物我关系的对待性,化人对物的有所待为无所待。以这无所待的心境欣赏出游从容的“鱼之乐”原是极自然的事,如此“知鱼之乐”之“知”是一种悟知,一种体味,一种物我相忘中的心之所感或情之所通。惠施与庄周之道术不无径庭,但以其二人终生为友而相晤论学可断言,其各自学术的个性里必有某种可视为二者之通性的运思的共感,而这通性的深刻或正在于其个性的灵动。《庄子·徐无鬼》中讲到这样一个故事:
讲述故事的庄周是自比于那位斧艺绝伦的姓石的匠人的,这当然可看出他那恣纵不傥的生命情调,而他把惠施比做那个面对挥动的利斧“立不失容”的为“质”者,也足见被其引为论辩搭档的惠施是何等沉着、从容而涵养深厚的人物。其实,庄周和惠施所以有可比之匠石与其质者关系的那份学缘,乃是因着庄周的“齐物”与惠施的“合同异”的卓识之间有着足够大的通而不同的张力。庄、惠的濠梁“鱼乐”之辩,惠施终究为庄周所屈,不是由于惠施的辩才不济,而是因为前者所持的“齐物论”在其言辩中是贯彻始终的,而后者却在不意中未能恪守其“合同异”的见地。
无论是庄周借孔子之口所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德充符》),还是他径直所称“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齐物论》),都表明庄周对惠施的“合同异”之说有所留意,亦有所汲取,但惠施对于庄周的“坐忘”(《大宗师》)、“心斋”(《人间世》)而至于“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天地》)的理致则未必了然于心,也未必能够以其“合同异”所可能有的局量予以包举,这彼此相知的深浅或许已经注定了“濠梁之辩”的高下。然而惠施的“合同异”究竟何所谓呢?
真正说来,惠施这一论题所指示的是“合同异”之说的适用范围,或“合同异”这一观念所能笼罩的领域,此即为“大一”与“小一”之间的“实”的世界。至大无外 —— 大到没有边际因而没有它之外可言的境地 —— 的“大一”,至小无内 —— 小到没有迹象因而没有它之内可言的境地 —— 的“小一”,是“大”、“小”的两极或所谓两个极端;这两极只能由下定义或作界说得到,不能从经验的世界中获取,因此,它们只能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中,永远不可能被我们的经验所证实。“大一”与“小一”只有“异”而没有“同”,两者无从讲“合同异”,也就是说,“合同异”的说法不适用于对“实”(实际事物)无所指的纯“名”(纯概念)或绝对的“名”(绝对概念)的领域。除此之外,“实”的世界或经验世界 ——“至大”与“至小”或“大一”与“小一”之间的世界 —— 中的一切,所有事物相互间的“同”、“异”,都是相对的,都可以“合”其“同”、“异”而将“同”、“异”作一体把握。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对这一论题,诸多学人的诠解并无异议,这里要分外指出的是“小同异”、“大同异”之分所强调的乃在于“合同异”的层次:经验事物的个体在“种”内的“同异”之辨或经验事物的“种”在其所“属”范围的“同异”之辨,是“小同异”之辨;“万物”各各相“异”,而相异的万物毕竟在它们各各为“物”这一点上有它们的相同之处,这样的“同异”之辨是整个经验世界的“大同异”之辨。“小同异”之辨是一定范围的“同异”之辨,亦即一定范围的事物之间既“同”又“异”的“合同异”之辨;“大同异”之辨是整个经验世界范围内万事万物既“异”又“同”之辨,也就是天地万物范围的“合同异”之辨。对于惠施说来,经验事物间的“合同异”之辨,既包括了对这一物与那一物、这一种物与那一种物、这一物与所有其它物在同一时刻的既“异”又“同”的分辨,又包括了对某一物或某一种物在这一时刻与那一时刻既“同”又“异”的分辨。因此,无论是“小同异”,还是“大同异”,都既可以在空间扩展的意味上去说,也可以在时间推移的意味上求取,从而,正可以说,所谓“合同异”之辨总是那种动态的时空视野中的“异”中求“同”或“同”中求“异”之辨。
):“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这个收摄前九个论题的论题,申示的是“合同异”之辨的价值内涵:既然“大一”与“小一”之间的天地万物都既相“异”又相“同”,那么,从相对的“同”处看,天地原只是“一体”、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人处在这样的“一体”世界中,就应该同类相惜、同体相爱而“泛爱万物”。“泛爱”是“合同异”之说的主题,是惠施所有“苛察缴绕”之辞的命意所在、谜底所在。这由“天地一体”而说“泛爱万物”,看似诸多论题因果必至的一个结论,实际上作为价值祈求赋有对于所有其它论题说来的前导性。它虽然只是在最后才被道破,却自始就默寓于各论题的具体演述中。
):“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破译这一论题的要害在于“无厚”一语,前人对此考辨颇多,但大都似是而非,不足为训。《庄子·养生主》中,记着一段庖丁解牛的故事,其中庖丁在谈到自己解牛的诀要时说:“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这话的意思是:牛的骨节相接的地方总有间隙,而锋利的刀刃却薄得几乎没有厚度,以这“无厚”的刀刃进入骨节间的空隙,游刃其中必有大得多的余地。冯友兰引用了这个典故,以“刀刃者无厚”的“无厚”解“无厚不可积也”的“无厚”,这对于论题的破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很快,他的思路就出现了歧误。他说:“无厚者,薄之至也。薄之至极,至于无厚,如几何学所谓‘面’。无厚者,不可有体积,然可有面积,故可‘其大千里’也。”(冯友兰,
页)当“无厚”最终被确定为“几何学所谓‘面’”时,他丢弃了他起初找到的那个出发点。事实上,惠施所说“无厚”是就经验世界的“实”—— 如“刀刃”的“无厚”—— 而言的,是对薄的东西的一种形容,不是指“几何学所谓‘面’”那样的纯“名”或纯概念意义上的“无厚”。冯友兰一方面认为惠施的这一论题重在强调“在形象之内”的“实的相对性”,一方面又把“无厚”理解为“几何学所谓‘面’”那样的“超乎形象”而非可“实”指的状态,这是他的逻辑的自相乖离。此后,学界探讨名家者,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几何学意义上的“面”理解惠施的“无厚”,如所谓:“平面只有面积而无体积,所以从‘厚’(体积)来说即使是至小的,从‘面’(无厚)来说仍然可以是至大的”(任继愈主编,第
然而,如果以“无厚”为“刀刃者无厚”那种对“实”有之薄的形容,而不是对几何学的面那样的“无厚”的称谓,那么,这个论题就应该作如下的解释:“不可积”—— 难以见到体积而几乎不可量度 —— 的“无厚”之物,仍可以使它薄而又薄,在动态的薄下去而趋近几何学的面时,它可以延展到千里之大。可以用“无厚”来形容的极小极薄的“实”物(如金箔、锡箔等),在上下维度上薄而又薄的动态延展中却在长宽维度或四围维度上可大到千里,这小大的相对正说明着“异”(大小有别)、“同”(同一个“无厚”之物)的相“合”。换句话说,这是小(厚度小)与大(面积大)的“合同异”。
):“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这里的“卑”与“比”相通,“比”有“近”、“靠近”、“亲近”的意思。因此,荀子也把这一论题转述为:“山渊平,天地比。”(《荀子·不苟》)唐人杨倞注《荀子》一书,在注“山渊平,天地比”时援引了一段话,他说:“或曰:天无实形,地之上空虚者尽皆天也,是天地长亲比相随,无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则天亦高,在深泉则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远近皆相似,是山泽平也。”这个被引述的“或曰”,对“天与地卑,山与泽平”破译得很透彻,后世学人凡所解与此多少相左者,可以断言,其亦将多少与惠施之学无缘相谋。胡适所谓“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是指“地圆旋转,故上面有天,下面还有天;上面有泽,下面还有山”(胡适,第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这是在说万物处在不舍刹那的时间之流中每一刻都在变化,不会有瞬息的停顿。在古人的观念中,地是静止的,“日”是不停地在大地上空依一定的方向移动的。依惠施的看法,不停地移动着的“日”在它刚刚处于天的正“中”的那一刻就已经在偏斜(“睨”),这正和偏或“中”和“睨”在太阳看似正中的一刹那同时存在于移动着的“日”。同样,“物”有“生”必有“死”,它的“生”的开始也是它的“死”的开始,“生”历经着一个过程,“死”也历经着一个过程,并且这是顷刻不离的同一个过程;物“生”着的时候物也“死”着,“生”、“死”在同一有生之物上如影随形。一旦“生”的过程结束,“死”的过程也就结束了,物“生”的刹那就是“死”的刹那,这叫“方生方死”。“中”与“睨”(斜)对于“日”相“异”而又相随,“生”与“死”对于“物”相异而又相即,这是“同”、“异”相“合”或“合同异”的又一个例证。
页),固然亦略近题中之义,然而,当他就此批评惠施“依然还是免不掉循环的观念”(同上)时,其所云则可谓与评说对象风马牛不相及了。杨俊光援引恩格斯所谓“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理解“日方中方睨”,援引恩格斯所谓“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而“生就意味着死”申论“物方生方死”,应该说是切中论题的,不过,他终究把惠施的说法视为对辩证运动观、生命观的“一种猜测”,则可能对古代中国人的独特智慧多少有所委屈。(参见杨俊光,第
)以来,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国学人往往以惠施已谙晓地圆说为预设来解释其相关论题。胡适指出:“惠施论空间,似乎含有地圆和地动的道理,如说:‘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燕在北,越在南。因为地是圆的,所以无论哪一点,无论是北国之北,南国之南,都可以说是中央。又说:‘南方无穷而有穷。’因为地圆,所以南方可以说有穷,可以说无穷。南方无穷,是地的真形;南方有穷,是实际上的假定。又如‘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更明显了,地圆旋转,故上面有天,下面还有天;上面有泽,下面还有山。又如‘今日适越而昔来’,即是《周髀算经》所说‘东方日中,西方夜半;西方日中,东方夜半’的道理。我今天晚上到越,在四川西部的人便要说我‘昨天’到越了。”(胡适,第
)联为一题以寻求答案。这个有趣的失误是值得一提的,它至少表明,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想要求得与古人心灵的相通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牟宗三认为:“‘连环可解也’并不是独立的一条,而是对前两句的提示。‘连环’是副词,《天下篇》言‘其书虽瑰玮,连犿无伤也。’语中的‘连犿’用字虽不同,但意思相同。‘连犿无伤也’意为‘宛转无妨碍’,‘连环可解也’意为‘圆转可理解’,也是个提示语,并不是独立的一条……‘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就是把宇宙看成圆的……惠施于此有个洞见,即‘宇宙是圆的’。”(牟宗三,第
页)这别出心裁的说法当然可以在名家研究中聊为一家之言,不过,比起前人的其它解释来,新提法的逻辑上的矛盾反倒更多了一层。如果“连环可解也”果真不过是“提示语”,为什么它只是被放在第六、七两论题后作“提示”,而不是放在第九论题后一并作“提示”呢?因为第九论题“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原是可以与前两个论题归为一类的。至于说惠施“将时空混一”,那完全是因为责备惠施的牟宗三把六、七两论题合而为一(“混一”)的缘故:如果对几个论题分别求解,那么,“时”原本只是“时”,“空”也原本只是“空”,所谓“时空混一”自然也就无从说起了。
把“宇宙是圆的”推想为惠施的“洞见”,似乎是得了“南方无穷而有穷”的真解,但当论题被框进一种科学视野时,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意趣也就被遮蔽了。战国时期的惠施是否已经有“地圆和地动”的“洞见”是不能轻率下断语的,而重要的是,由“无穷”和“有穷”所表达的“南方”的相对性也并不需要以“地圆”或“宇宙是圆的”为前提去解说。在惠施看来,任何一个被称做“南方”的地方对于比它稍南的地方来说都是北方,在“实”的世界或经验世界里,永远不会有绝对意义的“南方”。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南方”没有边际(“无穷”),所以无论怎样“南”的“南方”,都会相对地成为“北方”(“有穷”);动态地看“南方”,“南方”可以说到“无穷”远处,但在这动态的“南方”中,每一处“南方”又无不可以说是更南方的某个地方的北方。南方在“无穷”地延续着,而构成这无穷延续的是无限多个“有穷”的可称作某某地方的“南方”。
与“南方无穷而有穷”所表述的空间维度上的“南”、“北”的相对性相应,“今日适越而昔来”要告诉人们的是时间维度上的“今”、“昔”的相对性。破译这一论题的关键在于松开“今日”的执著。时光如水,原是刹那刹那都在流逝的。人们通常以“今日”、“昔日”计时,把时间分成有节奏的段落,只是为了生活上的方便;但习惯也往往使人们静态地看待某一时段,以致把这一时段与那一时段绝对地间隔开来。张默生说“今日适越而昔来”的说法“违反逻辑,不免涉于诡辩”,就是失误于今昔时段的机械划分。实际上,“日”在古代兼有“时”的意思,因此“今日”也可以解释为“今时”。如果以“今时”解“今日”,“今”与“昔”的相对就是当下的相对而不只是某个较长时段的相对。在时间之流中,“今”当下即是“昔”,才说是“今”“今”已成“昔”。时间的方“今”方“昔”,正好与“日方中方睨”的理趣相贯;才“中”即“睨”方有日影的移动,才“今”即“昔”方有时间的永无止息的流逝。“适越”在“今”,但“今”在刹那间即变为“昔”,由“今”、“昔”的刹那转换领会“今日(时)适越而昔来”,并没有逻辑上的不通,称这一论题“不免涉于诡辩”,实在是委屈了论题的提出者的灵动的智慧。
庄子对惠施的学术有“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天下》)之叹,但他毕竟没有轻忽惠施之学在当年有过的所谓“儒、墨、杨、秉四,与夫子(指惠施 —— 引注)为五”(《徐无鬼》)的风行一时的影响。同样,荀子也曾苛责惠施“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荀子·非十二子》),而他却仍不能不承认这些琦辞、怪说“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同上)。倘不囿于庄、荀所言及自此以降诸多学人陈陈相因的成见,惠施的那些煞似怪诞的辩言其实是可以重新评说的,尽管深藏其间的灵动智慧早已是往世的绝响。
)惠施虽“以善辩为名”(《天下》)而被称作“辩者”、“察士”(《吕氏春秋·不屈》),但其所辩所察终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所谓“万物毕同毕异”的“合同异”当是其“历物之意”的逻辑枢纽,而蕴含于逻辑进退中的价值取向则在于一体天地而“去尊”(《吕氏春秋·爱类》)以“泛爱”。那些被认为“逐万物”或“散于万物”的论题 —— 诸如“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等 —— 不过是就近取譬的种种隐喻,其辞散,其意则不散,在看似“逐”于“万物”的言辩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爱”的规劝。对这一份“爱”不能了悟,则不足以讨论“合同异”,更不足以评说以辩难“合同异”为能事的惠施。
早期杂家人物尸佼曾撮其要论列他视野中的先秦各家说:“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弇于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纯、夏、怃、冢、晊、昄,皆大也,十有余名而实一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尸子·广泽》)他当然不可能品评比他晚出的惠施,但没有问题的是,为惠施所推重的“去尊”、“泛爱”则略与“兼”(兼而爱之)、“公”(天下为公)、“衷”(中正)、“均”(均平)、“虚”(不执著于任何一物)、“别囿”(不局限于任何一隅)相通。“兼”、“公”、“衷”、“均”、“虚”、“别囿”和“去尊”、“泛爱”皆为价值范畴,而非认识或知解范畴;它们名称不同,但祈向公、正、均、平的价值追求实际上确有一致之处。惠施没有明确提到儒、道、墨三家皆有称说的“道”,但处于人文眷注的重心在老子、孔子之后由“命”向“道”转换的时潮中,他不可能不受其陶染。他“遍为万物说”,而所说并不牵累于与利害相系的“命”;他倡导“泛爱”,这“泛爱”必至于为关联着人的心灵境界的“道”所笼罩。诚然,“道”对于惠施尚嫌朦胧,并不像它在儒、道、墨诸家那里虚灵而可辨。
)同是倡说一种不落于褊狭的“爱”,墨子“以天为法”(“法天”),取法“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墨子·法仪》)而鼓吹“兼爱”,孔子由一以贯之的“仁”道教诲人们“爱人”(《论语·颜渊》)而“泛爱众”(《论语·学而》),惠施却是以“万物毕同毕异”的“合同异”之辩论说“泛爱万物”。单从字面上说,惠施所谓“泛爱万物”似乎与孔子的“泛爱众”之说更贴近些,但“泛爱万物”之“泛爱”是从一种道理讲起的,而“爱”就其根柢而言却并不就是一种道理。孔子所创始的儒家之学由“亲亲”讲“爱”,这“爱”缘起于真切生命中的一种自然而然、油然而发的“情”。“亲亲”之“爱”以情相感,可从“老吾老”顺着人情之自然推及“人之老”,从“幼吾幼”顺着人情之自然推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爱”而及于“人之老”、“人之幼”,此“爱”即是“泛爱众”。由这样的“泛爱众”进而相推,以情相感的人对人的爱可扩展至情及于物的人对物的爱,于是儒家之“爱”便有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局度。“亲亲”之爱、“仁民”之爱、“爱物”之爱,这是一个“爱”有“等差”的过程,然而如此的“等差”并不构成“爱”的止碍,反倒显出润泽于“爱”中的情之自然。由“万物毕同毕异”的“合同异”证衍的“泛爱万物”之“爱”,没有情之自然所呈现的等差,它犹如墨家的“兼爱”,在把普泛的“爱”讲成一种应然的理时,削夺了“爱”中自然而本然的那份情愫。
墨子以“天志”为“兼爱”的终极依据,“兼爱”最终所遵从的是他律(以他在的“天”为“法仪”)原则;孔子把“爱人”而“泛爱众”的那种情怀归结于人心中内在的“仁”,由“亲亲”到“泛爱”所凭借的是“人能弘道”(《论语·卫灵公》)的价值自律。但无论是孔子还是墨子,在“爱”的祈向上都有“形而上”的信念,尽管墨子的“天志”所指示的是某种外在超越的形而上学,孔子的由“仁”而“圣”的“中庸”之道(执“过”与“不及”之两端而用其“中”的修养之途)所开辟的是一种相契于生命体认的价值形而上学。惠施是取论理 —— 辩说“物”理 —— 的方式对“泛爱”作论证的,这使他终于与形而上的祈求无缘。少了形而上眷注的“爱”没有它的极致情境或理想之境,缺了这种极致情境或理想之境的论理无从立以为教而引导天下的风化。
诚然,惠施的论题将人们惯常认可的某些道理“否定”了,但问题在于那被人们视为常识的道理是否是“一个真的道理”。如果一个人们习焉不察而确实有问题的道理被“弄得动摇了”,动摇这道理的言辞一定会使人们感到“怪”、“琦”的,不过这带给人们“怪”、“琦”的或正是一种富于创意的东西。事实上,常识总是把“中”与“睨”、“生”与“死”、“南”与“北”、“今”与“昔”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依这种静态的没有转换的对立为前提,人们对时空、事物、境况的判断往往取“非此即彼”—— 非“中”即“睨”、非“生”即“死”、非“南”即“北”、非“今”即“昔”—— 的态度,而在这态度中起作用的是多数人日用而不知的形式逻辑。惠施以“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时)适越而昔来”的论题,把“非此即彼”的判断转换成了既“非此即彼”又“亦此亦彼”(亦“中”亦“睨”、亦“生”亦“死”、亦“南”亦“北”、亦“今”
)在惠施“历物之意”诸论题留给人们的智思遗产中,取“譬”这一言说方式分外值得一提。除开“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三题外,惠施其它论题无一不是设“譬”而谈,而且这些譬语大都是隐喻。刘向《说苑·善说》辑有一段惠施辩释“譬”这一言说方式的对话。其云:“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可见,“譬”的设用原在于“直言”难以“谕”其意。取“譬”出于说者达意的不得已,这不得已透露的是“直言”的局限,而惠施辩“譬”则正表明了他对“直言”所固有局限的觉知。
“直言”是纯概念性语言,它由表达抽象共相的语词依语法连缀成句,又由若干这样的句子构成有序的话语以言说。这样的言说借重语词的相互规定、句子的相互制约把某种意思陈述出来,总的说来属于与结构性思维相应或与结构性思维一而不二的结构性表意。表意的结构性注定了其所表之意的非动态、非有机、非整体性,而惠施既要述说那种赋有动态、浑整性状的“亦此亦彼”的道理,便不能不舍“直言”而取“譬”语以另谋言说蹊径。“譬”把人带进一种情境,使人以其全副阅历去感受、体味设“譬”者所感受、体味到的意趣,这意趣得以整全而非支离、生动而非孤静的传递乃在于非可解析的生命的感通。当柏拉图说“除了靠举例,阐述任何较重大的思想都是困难的”(柏拉图,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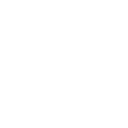

@HASHKFK